凝视女像:近年女性题材影片研究
来源:电影艺术 作者:李彬 时间:2014-09-01
近年来,十几部电影不约而同的或是用美人的名字或是用指涉女性身份的名词来命名,女性特质浓厚,影片中的女性,从小女孩的清纯暗恋到成熟女人的情爱追求,我们几乎看到了女人从成长到成熟的全部过程,而影片述说的无一不是女性的“成长”,在情与性的阵痛中成长。
人类文化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建构的,但又不可避免的被男权化和异性恋化。于是男性和女性就在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中、在对立与统一中寻求各自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男性往往成为女性梦想与成长的载体。

《孔雀》中的姐姐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现实的平凡让她压抑,直到有一天,姐姐看到伞兵从天而降,在这个男人身上,寄托着她逃离现实生活的一切。多年之后,偶遇当年的军官,曾经的英姿勃发沦为如今被生活磨蚀得猥琐平凡,她的梦想才被击碎,才开始真正明白人生的含义,于是痛哭;《暖》中,暖可以选择自己的爱情,却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暖的命运需要男人的爱情来改变,她最后嫁给了放鸭子的哑巴;《情人结》里的屈然只有在漫长的等待中坚守对爱情的信念。在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屈然寂寞的等待着,渐渐老去,直到失去了力气。
在这些影片中,爱情承载的是女性主人公对于新生活的梦想,这种新生活不存在于当下她们的生活可能里,而存在于她们的梦想中,这梦想借由于男主人公的爱情来实现,却往往落得失望的结局。
与情人相反,父亲这一形象,却往往成了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对立面。
当父亲是缺席的,父亲死了或遭到父亲的遗弃,女性在其情感历程中苦苦追寻爱情对生命的价值,爱情的意义胜过了生活中其他一切事物(《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仿佛只有拥有爱情征服爱情才能证明生命的胜利(《美人依旧》);只有爱情带来的那份温暖才能填补亲情的空白(《茉莉花开》;生病的父亲(《美人草》)、对女儿的命运无能为力的父亲(《暖》)、忙于生计而麻木的父亲(《孔雀》),这些父亲虽然在场,但抚慰不了女儿成长的痛苦和惶恐,这些女孩们自己在生活中闯荡,她们个性独立,敢于标新立异。但当她们的爱情憧憬破灭之后,她们都快速成为了主妇,无奈的,假装安分守己地生活着。
成长于一个有着强有力的父亲的完整家庭的女性则难逃父权的专制,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爱情的自由就要努力冲破父权的樊篱/封建的桎梏/传统的压迫。《情人结》的屈然,《青红》的青红,父亲的在场带来的却不是成长中的关爱和呵护,而是父权的专横下导致的青春残酷记忆。
至于徐静蕾的《我和爸爸》当属特例,虽名为父女情,但“父亲”的特征要少于“男性”的特征。父女两人的对白更像情侣在调情。对此,导演本人也承认了这种潜意识的“恋父情结”的存在。而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这部名为女人的故事的电影其实仍然是“我”和“父亲”的故事,姜文饰演的男人是徐静蕾饰演的女人精神上的父亲。影片爱情的实质仍流露着这种“恋父情结”。
女人:时代的符号
人是社会的人,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的命运更脱离不了大时代的背景,不同时代的女主角面临的困境也因此各不相同。而女性故事一旦与“时代”挂钩,就很难逃脱“命运”二字的纠缠,也就难免逃脱“符号”的嫌疑。
解放前。在人们的概念中,似乎解放前的女性形象非穷苦即腐化堕落,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阶级对立的状态。但在近期出现的电影中,阶级的对立不再成为时代标志,相反,“解放前”的时间概念由于其笼统和模糊,成为了导演有意选择的时空背景,以淡化故事主题以外的元素,为讲故事营造一个虚化了的时间元素。
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最初想放到现代来写,但是写不下去,后来“放到30、40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面去。”
《美人依旧》导演胡安这样阐述:“因为我想表达的是两个女人和同一个男人之间纠缠的爱情和分裂的性格以及难舍难弃又不得不弃的无奈。”“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大到现代的生活中,把它浓缩进30、40年代,说起来会更自如。”
导演们没有讲述历史的雄心壮志,他们所要制作的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陌生女人,《银饰》的碧兰,《美人依旧》的姐妹大小姐璎子、二小姐小菲,这些女性她们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没有时代局限性的个性解放的特征,甚至可以是任性的。
文革和文革后。文革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命运,个人的命运被政治话语改写,即使文革结束,对历史的无奈和恐慌仍然残存。《美人草》和《小裁缝》两部同为描写知青生活的电影,但两部电影都不过是借时代营造一种气氛,并无对特殊年代特殊人性的深刻挖掘。那些本来是戕残人性的苦难经历,那段本来苦涩的情感,因为对女性的窥视与玩味而弥漫着一股异样浪漫的轻松情调,变得让人向往,成为市场的卖点。这种对苦难理性反思的放逐,对女性的异样玩味,是当下消费社会在文化表象上的显著特征。
而文革后,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的《青红》和《孔雀》却有着隐约书写历史的抱负。顾长卫说:“《孔雀》这部片子反映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王小帅的导演阐述说:“这个电影带有了我过去生活过的那个地方的些许印记……我想用这部自己一直想拍的电影来献给我的父母和那些和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人们。”
当代。确切的说是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的压力渐渐散去,人们不再是政治的动物,生活开始呈现它的多义性。
《周渔的火车》的导演孙周说:“我们中国发生了那么大一个变化,我们的中国女性开始真正意义地,开始去寻求自己的那份感受,去寻求自己的那份需要……其实整部电影我是希望建立这么一种镜语关系,所谓镜语关系就是这两个男人就像两面镜子一样,令周渔通过和他们的一个互相关系发现自己的需要……”
而在《恋爱中的宝贝》里,宝贝这个精灵古怪的当代城市少女,其实是这个城市一切关于现代的符号,而女孩的成人仪式,甚至成为社会物质文明现代化到来的标志。在尘土漫卷飞扬、碎石滚落四溅的地平线上,万丈高楼层层叠叠拔地而起。这些让人全身颤栗望而生畏的钢筋水泥怪物,带着更为令人恐惧的喧嚣与野蛮,瞬息之间完成了所谓的现代化,同时让女孩在瞬息之间完成了成长。
立场:玩味还是自恋?
如此纷繁的女性影像,似乎可以表明,新一代电影人开始关注女性,关注女性成长,其实细细研究下来,却并非如此,我们依然难以见到对女性生存状况的现实描述。在中国导演的影像世界中,女性更多的是一种标签式的,概念式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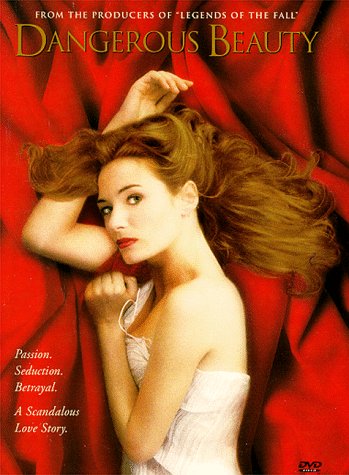
从电影中女性叙事到女性意识到女性角色的阐释,也许更多来自某种习惯性的社会意识与文化心理的积垢。在电影中,自觉地把社会性别意识渗透在内容中并不常见。被公认为女性主题探索片典范的《大明宫词》导演李少红谈到,女性导演可能会把女人当作一个“我”,而男性导演则会把女人当作一个“她”,两者关注的角度和方法不一样。相比较之下,男性导演在拍摄类似女性题材时,更容易采取一种“玩味”的态度。
人类文化是男性所书写的,而女性似乎只能被书写,被男性和男性文化所书写。一个男性导演往往容易对女性进行简单书写。大多数男性作者塑造女性形象,不外乎两种目的:借此满足自我性幻想的需要,或者投射自己对某种女性特质的评价。
比如对女性美的玩味。《小裁缝》中,对“小裁缝”身体的“偷窥”,使得女主人公作为色情奇观、作为被看者的意义不言而喻,印证了女性的性观赏价值和色情意义。《生活秀》则一改池莉小说中生活现实味很重的人物和故事,用唯美的手法着意强调了女主人公的风情。
对女性对男人痴恋的玩味。导演孙周一直强调,从《漂亮妈妈》到《周渔的火车》,他一直都在尽可能令自己的观点往女人的角度上偏移。但是,也正像孙周自己所言,他改变不了自己先天的男性立场,所以,影片《周渔的火车》中难免有一种暧昧的玩味,玩味周渔的风情万种,玩味周渔对爱的执著。其实,《生活秀》、《周渔的火车》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都带一点沾沾自喜的男性心理,百般玩味,无限回味一个美丽女性对男性的爱断情伤。
对男性救赎女性的玩味。男性往往是女性梦想的载体,反之,男性则承担了对女性的救赎。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承担了文化启蒙的功能,《暖》中,井河曾答应过暖带她离开家乡;《孔雀》中,伞兵军官也是作为另一种高于现在生活的代表;《小裁缝》里,更是以对小裁缝的本真生命、自然天性的否定为前提来完成对她的文化启蒙和精神改造。而其启蒙、改造的过程又不无渗透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男性意识对女性意识的改写、男性秩序对女性世界的侵略。
而女性导演,往往又会陷入另一个怪圈,那就是“自我”。女性导演自觉地以一种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自身与外在世界的成长经验,这种努力在其作品里,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从强调女性自身经验、想象和欲望出发,在电影创作中创造了一种极端强调个人化的生存感觉和女性的独特品质的语言方式,并以此种姿势重新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确认和定义,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
李少红近年来作品非常女性化,《大明宫词》、《橘子红了》都表达了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但就情节和叙事来讲,很难想象《恋爱中的宝贝》出自一个成熟的中年导演之手,更象是新生代的叛逆宣言。但就影片的反响来看,不能不说,李少红是陷入了一个自我乃至自恋的窠臼。
徐静蕾将陌生女人的爱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上看,电影似乎通篇渗透了女性意识,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享受我自己的过程。至于得到得不到,至于男性的反应怎么样,跟我个人爱的过程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是这样,既然就是一个女人自我完成的过程,那么这个男人哪怕就是一个石柱好像也可以完成了。
由此看出,当下的女性导演虽然有了女性意识表白的欲望,但仍停留在自我展示的阶段,她们还没有重塑自我的自觉和勇气。
实力派女导演宁瀛的新作《无穷动》对传统女性的审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宁瀛将片名解释为“女人无穷涌动的,欲望的体现”,影片是自己“对现有的东西深恶痛绝时做出来的,是面对现有文化市场到了怒不可遏的情况下的一种反抗。”至于男性观众能否从中感觉到片中女性的魅力,宁瀛则表示,男性观众的反应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恐怕又是另一个极端。
女性:生存在何处?
很多年前,导演周晓文曾经说过:“我所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女性,是今天生活着的女性,她们当下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她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认为她们脑子里的许多想法是要落空的……我认为她们是盲目而现实的。现实指的是她们对生活的一种基本态度,她们要在眼下得到自己的快乐,所以她们要现实一些。这一切证明她们并未出身于女权社会的理想空间。她们自认为自己是果敢的,是坚定的,是不依附于男人的,但她们的行动往往与她们的结果相反。”可惜到目前为止,这种关注与反思在中国大陆电影中仍然太少太少。
侯咏的《茉莉花开》曾经被标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题材影片,但是,三个时代的三个女性,就像是三个时代标签,导演倾向于将人物的内心外化,再加上刻意将三个女人的故事进行对比,使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叙事显得局促而匆忙,人物形象便显得单薄而缺乏张力,变成了一部略显沉重的,主题先行的影片。
相比之下,同样是描写三个时代的女性,美国影片《时时刻刻》中,“三位女主人公或是忧虑女性无自我的社会从属性,或是无法承受家庭日常琐事的乏味和压力,或是以假象自欺;面对与内心真正的自我相悖逆的生活处境和社会责任,她们无措、崩溃或自戕。”女主人公们都渴求更有意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并用行动表明了她们的决心,虽然过程艰辛曲折,却也都一步步迈进了独立(精神上或物质上)的自主生活道路。
台湾导演张艾嘉的《20 30 40》在突显不同年龄女性的独立精神之外,带给观众一种层次渐进、心境转换的成长历练,带出女性不同阶段所遭遇的类似问题(不再是实际年龄的问题,而是一种活在现世无可避免要思考的问题),来谈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几个阶段问题,同时希望能扩大诉诸每个观众的普遍性,让所有观众都能从这些女性角色当中获得其中一部分的自我认同。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侯咏的《茉莉花开》意在通过三个女性命运的对比,彰显“花”作为新时代女性独立自强的风采,然而,就如同第五代导演电影中的理想女性一样,所有的意义恐怕只是在于为导演的主观意念服务,完成导演所设定的主观必然性的呈现,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导演手中的道具,成为导演的代言人。
女性电影:可能性
按照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观点,真的能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是要通过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的生存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揭示特定时代和地区中之不同女性的心理特征和共同需求,为她们自由地表达观点,抒发心声,解决困难,选择道路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
由此,以上多数影片虽然在声势上以“女性电影”“著称”,但这种“女性”更多的是商业噱头而已。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寻觅那些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电影,因为笔者并不认为,空洞地将价值观的好坏仅仅以“男性”和“女性”的区分作为判断的标准,认为女人一定要独立于男性或者一定要割舍爱情或对婚姻的渴望才能够表达女性的独立意识或自我觉醒,笔者所希冀看到的是,能够书写当代女性的现实境遇的影片,真正的关键在于能否表现出女性正视自我的情感需求以及心智的成长历程。
例如早先香港的《女人四十》、《虎度门》,40岁女人的琐碎生活现实,以及面对事业与生活的取舍;20年前严浩在《似水流年》中塑造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女性,心事的复杂与难以名状;而近年来台湾电影《落鸟》中对于留守太太的面对“情”与“欲”的选择;《女人女人》之《秋天的蓝调》中一个疲惫淡漠的中年女人,面对丈夫情变的十分真实可信又传神地表达……凡此种种,在大陆的女性题材影片创作中,实在是有所匮乏。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国内尚有几部对女性生存境遇刻画颇为到位的作品。《假装没感觉》于平凡琐碎的生活实例中,印证了女性主义对于“自己的房间”追求,生动而深刻地探讨女性对生存与精神空间的寻找与探求,以及三代女性之间的亲情与矛盾,让人体会到创作者表达人文关怀的企图;《哭泣的女人》中,当男人依靠不上的时候,女人便要承担更多的生活责任,她是被孤零零荒置在这世界上,没有人需要她收留,也没有人收留她。于是在一片茫然面前,她终于号啕大哭;李玉的作品《红颜》,同样是山城小镇的女性故事,较之《生活秀》更有生活质感。
而最能表达女性自觉意识的,要算是青年导演王全安的影片《惊蛰》了。影片描绘了一个农村女性关二妹,在她自发的追寻心中目标的历程中,既有被动性也有主动性,她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是更全面客观意义上的人物,更为接近人之为人,女之为女的本来自然的面貌。
结语:期待
影视已经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多重挤压下背负着浓重的廉价特征、形式主义和消费色彩。很多国产影片以女性电影自居,打着女性的招牌,却大多在女性的生活层面浅尝辄止,少有真正能深入女性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创痛的,几乎没有触及女性最根本的需要,电影塑造的女性角色只是几个令人同情,或者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女性”只是一个题材范畴而已,很少具备现实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女性主义终极关怀的目的显然不是要让女人在现存的象征秩序中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力,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替换游戏,也不是让女人在婚姻和事业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让女人从原有二元对立的参照系中跳出来,通过自己的坐标与航道到达希望与自由的彼岸。
女性电影是一个大议题,更多,更真实的国产电影的女性书写方式值得被期待。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支持公益传播,所转内容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告知,我们会立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