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沙泥 · 遇见女性
来源:女性艺术家 作者:廖沙泥 时间:2023-10-20
在艺术史的漫漫长卷中,女性常常作为被观看和描写的对象,作为“她”者被书写或解读。女性艺术家以及作品的能见度,作为被观看与书写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远高于“她”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身份。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其所敞开的女性价值空间的提升,越来越多以创作者身份参与到艺术中的女性及其作品,浮现于大众的视野中,她们作为艺术中的观察者和创作者,留下了“她”为第一视角的思考、感知和表达。对于“她”视角的打捞与呈现,试图以自我书写的角度,展开女性艺术家在社会进程中的成长曲度以及对女性身份自我认知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艺术家的成长与个体经验与时代洪流密不可分。在相当长一段的历史时期中,女性与家庭生活深度的绑定使其社会参与度与艺术参与度相对狭窄。女性参与艺术隐而不彰的现象,直至近百年来才逐渐有了本质性的变化。
追溯明清时期,我国的古典绘画中已然出现过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集中表现。伴随着手工业与外贸通商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活跃的文化氛围和思想的激流。女性的社会价值开始被重新认识,其中,具有文化话语权的文人及鉴藏家如董其昌、汪珂玉等,亦关注到女性绘画的艺术审美,开始在其作品上进行评论、题跋,部分印证了社会对女性介入艺术创作的认可。然而这一时期,女性的艺术创作长局限于闺阁生活背景,面向对生活和情感的摹写隐喻而内敛,使得“她们”的艺术表达仍然十分有限。
近代以来,由学权开始的女性社会权利的逐渐开放及日益普及,使女性受教育比例大为提升。而随着新思想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于不同维度,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分工,重新认识自我价值,成为历史进程的深度建造者和见证者。在艺术创作领域中,随之涌现出女性艺术创作的一个新的浪潮。“她们”的创作维度更加丰富宽广,不仅有对社会历史的纵向思考: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化间的思辨;同时也出现更多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在艺术创作中逐渐成了一种主体视角“观看”的自叙事。然而仅仅是作为“观看”的主体与女性意识的自觉之间还有着一段距离。在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中,这种“观看”在望向自身时,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长期潜伏于视觉文化历史中的,男性对女性观看的审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汇入中,女性意识的自觉在城市扩张与社会流动性的发展中不断向前推演。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视角开始成为“他”者目光之外的自我表达。这样的视角既是外向的,也是向内的,外向于女性艺术家对外部世界思考与探究,内向于她们对自我情感及不断生长的身份的自我审阅。
在此需要厘清,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不等同于女性艺术,亦并非所有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都蕴含对女性主义的讨论。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自觉与生长,“女性”,不停留于相比较于“男性”抽象概念之中,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它逐渐成为对女性特质的自我肯定。在艺术创作中,女性艺术家的视角不仅共情于不同社会身份中的群体,同时也具有鲜活的个体特征,而这种体悟和认知更是在流动的生命体验中不断生长。她们的创作将视野投入对现实的关怀,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着私密的情感变化。“她”是女儿,是姊妹,是伴侣,是母亲……基于生命体验的差异,女性艺术家呈现出了与已有的艺术史叙事别样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如果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样的表达,能见度微弱,那么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场域中,则浮现出越来越多维的她叙事的表达。而对散落于过去时光中女性艺术家创作断章的重新整理和回顾,则补充了我们对历史、生命、时间的理解。在此,艺术已然成了一种经验和记忆的载体,折射出愈发丰富和饱满的女性形象。相对于男性话语主导的历史书写,女性艺术家在不断地自我书写中,充满了内在的、生长的生命力量。她视角的打捞于浮现,丰富了女性的形象也丰富了历史的表述。
广东美术馆在展览策划的基础上,收藏了一批不同时期的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在此基础上,展览“她叙事——藏品中的女性视角”形成了最初的样本。展览试图以馆藏中有限的历史断章,勾勒出大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作品中女性视角的丰富线索:她们关注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关注社会的百态,关注处于关系之中的女性角色与感悟;于时代中清醒发声,或融于大潮,或独立意见;不自觉或自觉地流露出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对生命体验展开细密而透彻的思考。

“我可能不合潮流,不合时宜,不够深刻,甚至不识抬举,但,我想其实生活和艺术都是一种选择,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你有选择权选择,那么你选择什么呢?”——郑爽,节选自《我的选择》
展览共分为三个板块,“个体中的她”“观察者的她”“关系中的她”。在波伏娃《第二性》中强调了“女性”是被塑造形成的社会人格。换言之,女性的权利与自觉的意识互为因果,当女性的地位开始不再从属与依附的时候便开始有了自觉和选择的权利。这样的自觉也许不是女性意识层面的自觉,但是它关乎于自我表达与独立思考。当艺术家与时代互文,在时代浪潮中,成为一种涌现是一种选择,而坚持自我的内在抒写怎是另一种选择。在展览“个体的她”的板块中,尝试用艺术家的作创来回应她们对于内在自我的坚持。如郑爽笔下日常中平凡的小事,阳光、树木、花朵、生灵……这些大自然的动人细节。这几幅黑白木刻版画,仅有掌心一般的尺寸,最小的作品《小猫》只有 2.5cmx4cm。于是,“真情、自然、朴素和美”便是她的选择,也是她投射在画面作品中的自我造像。这一系列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作品中没有她幼年时颠沛的慌张,亦与同年代中火热的时代主旋律创作别样。它们小巧却冲合淡泊,在时代激情相映衬下愈发自然而冷静。它们不急不躁,她不慌不忙。作品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恬静的味道。无名画会作为非官方艺术团体,其自发形成的对现代艺术探索的活动,长时间被遮蔽于 20 世纪 6、70 年代的艺术书写之中,他们对于风景与“纯艺术”的追求,和“美学独立”的表达,在学者眼中,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反媚俗态度。是个体的、精英的;自然的,自我的。王爱和作为后期无名画会的参与者,她笔下的花天真如本人。有别于时代宏大的历史语境中作为配角颂扬的鲜花。
王爱和仍以笔下各类的花以表对美和理想的向往。花的美与彼时的现实相对,格格不入,却有着独立于时代自我坚持。她笔下的风景也并非写生,而是脱胎于写生地对理想的造像。彭薇的《Hi-Ne-Ni》名字来自希伯来语,意为:我在这里。作品是一件女性躯干的半身纸塑,上面绘有古典工笔的情节图式。此中,有深厚的传统文脉和艺术修为,但同时,她直白又脆弱的女性身体的造型,又是一当下立场的存在宣言:在这里,“她”在这里,“我”在这里。从艺术语言的形式上,它的宣纸与白描来自传统,而纸塑的形象又独立于传统;从精神中,围绕着女性身体的是传统道德、欲望和身份解放间不同视角的观看,它被直面,被审视,存在便是兀自独立于被观看的挣脱。这个抽象的女性形象放置于时间的坐标系中,是沉重又轻盈的,纠结而复杂的,古往今来,被不断讨论,也不可被忽视。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拒绝宏大的气势,可能小时候相当英雄太累了,所以对身边细小琐碎的事情更有兴趣。”“选择的都是它的日常性。”——喻红,节选自《时间内外》
在“观察者的她”中,展览试图展现女性艺术家向外关注的视野,她们关注社会,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她们以其敏锐的感受,捕捉社会的景观细节,对现实投入富有情感的目光。如庄晓的摄影作品,虽以几近客观、真实的方式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互助组、人民公社等不同的阶段的图景,但画面之中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舒展的人情与温暖;而雷梦君的摄影则记录了城市景观的变化中人们对身份的不断自我审视。她的作品善于捕捉与时间逆向的生活痕迹,往往浓烈的情感突兀于正在逝去的细节之中,城市的变迁于时间之中,往昔不再,而褪色和新生不断往复,作品仿佛一曲曲城市的挽歌与恋曲,长久回荡。有别于客观和感性的两种创作方式,在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叙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容了女性主题,画面中的女子的形象,往往成了人群景观的主体。由关注个体面貌进入到关注到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社会框架中进行思考。在展览中,喻红的作品《她——退休工人》是《她系列》中的一件作品,艺术家将照片与绘画并置,透过人物个体的空间关系的变化,透视出以为退休工人的生存状态和时代命运。图像的重叠,强调了时间的交错下对图像的反思,而家庭空间的叙事所建立起的人物的日常细节,消解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宏大叙事。从而,通过个体的“她”,折射出群像“她们”的生活体验,折射时代的变化。“她们”也许不是英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位,却生动于历史、记忆和存在。
心理学家米勒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系中的自我”的发展概念,并认为“关系”中身份的变化贯穿于女性身心成长的始终,并且在“分离、自主性与依赖性”间共存。在第三个板块“关系中的她”中,展览试图在向内关系的自我观照中,寻找到一种解读女性视角叙事的线索。“她”是女儿,是姊妹、是伴侣、是朋友、是母亲……而在一系列关系当中,南希·弗莱迪认为“母女关系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它与生育紧密相连,并且由此发生着角色的变化。母亲由女儿的成长而来,而在下一个阶段,女儿也变成了母亲。在母女的轨迹中充满 了陪伴、亲密连接与个性化间的撕裂,而在女儿步入于母亲身份的阶段,又在撕裂之后产生和解。它折射出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自我剖析与反思。展览中呈现了蔡雅玲的一组作品《polka dot-white》和《polka dot-black》。两件等大的架上装置,由 20世纪 80 年代所盛行的的确良布面为底绷紧画框为底。这熟悉的布料同时也是女儿(作者)的儿时记忆。两件作品,布面一方黑,一方白;在白色底上,均匀等距地用女儿的黑发绣上阵列的圆点;而在黑色布面上,同样的圆点则是由作者母亲的银头发绣成。两幅作品相应而生又相互回应,仿佛时间之中,被倒置和转变的母女关系。头发生于体肤,亲密、普通,柔韧又脆弱,会脱落,也会重新生长……可束紧,亦会散落,缠绕时有着挣扎与依恋间矛盾的张力。在作品中,在看似等大的圆点中,可以是时间的标记,也可以是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青丝与白发的缝绣手法各有性格,远看相似但细看决然不同,正如在生命经验下的一种和解,这也是一方延续,或是一方新生。
“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但是我们却发现了绘画;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我们正在用图画来描绘自身;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将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将用笔锋上的色彩预言未来的盛象。”——王琰,节选自《画梦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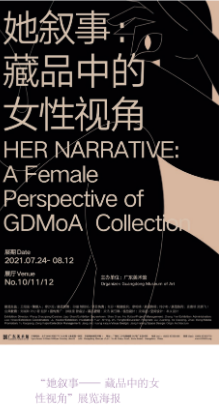
本次展览虽没有突出时间线索,但不同时代下作品所呈现出的变化,也够构成一条隐线的观察。随着社会的发展,千禧年之后,无论是从参与创作的人数还是作品的能见度上,都反映出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日渐繁盛。她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不仅体现在对大尺寸作品的创作中,还是体现在对新媒介的自由探索中。她们更加敏锐地关注自身、关注社会议题同时也关注技术的发展。对于新媒体作品的呈现不拘泥于技术迷恋的表象,而尝试在反思技术语言之下的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情感。展览中呈现了王琰2·1 米乘以 5·5 米宽的架上绘画《四月之一》,作品占据了整面墙体空间,以强烈的色块和恣意的长线条进行绘画书写。舒展而强大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而曹斐的影像作品《三元里》则以当时新锐的混剪手法,记录了城市发展中人们的迟疑和变化。它一反传统的影像叙事,有着鲜明的碎片化的风格处理,那些会被城市化进程的齿轮一带而过的情绪和细节,在作品的影像语言中,变得生动而共情,荒诞也幽默,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
于此,女性艺术家于今天的创作,一方面有意忽略由性别身份所带来的关注,努力让作品的艺术价值成为被关注的意义焦点。另一方面,她们更愿意肯定由女性特质所产生的作品的独特表达,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女性艺术家对技术与虚拟世界的关注,部分表征了时代对未来的想象。而难以回避的对女性命题的思考,于创作者本身,也有着自觉和不自觉地差异,同时也存在着不断再深入和变化的过程。它随着经验和理解不断地流动性地生长,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的维度的自省和观察。经历过对父权和平权结构性的反思,今天我们再谈及女性,更加是在以“女性”的独特性作为自我为坐标,在强调、肯定女性特质的基础上的自觉地进行自我抒写。这是主动的,是自信的,这也是这个展览想呈现的。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支持公益传播,所转内容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告知,我们会立即处理。